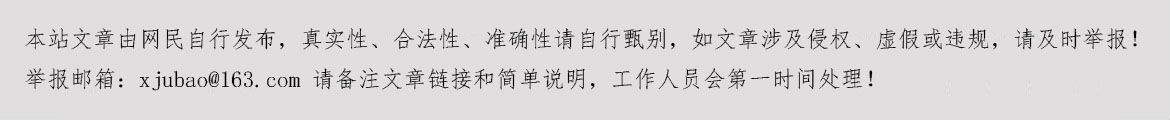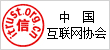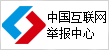“二奶”转行:终生制变分段制,私生子入学无门!
2021-04-04 10:00:00
15个月后,也就是2002年4月,我重访海湾村,竟有恍如隔世的陌生感。天气渐渐炎热起来,村内的走道两旁,又新开了三四家港式茶餐厅。缤纷嘈杂的音乐从各家餐厅的窗口流泻出来,纠结着在不超过3米宽的狭窄小道上横行。这个村子没有太多的改变,我的心境却改变了——那些“二奶”们,我的曾经的好友们,除了佳佳外,阿灿、阿婷、阿金、阿银、阿妹、阿春、阿月、我的邻居阿艳,还有启发和引领我走进“二奶”群落的“病友”阿洁,全都人去楼空,像一缕青烟般悄然而逝。听人说,阿灿、阿洁、阿银、阿妹、阿春、阿月都去关外的工厂企业打工去了。这真是令人兴奋的消息!不管她们现在是不是还在做“二奶”,只要她们离开“金丝笼”,能够到自食其力的天地里飞翔,只要她们在打工流汗,我就由衷地为她们感到高兴。我觉得,“二奶”们能够外出打工,是摆脱“二奶”樊笼,走向独立生活的第一步。
幸好佳佳的手机号码未变,我终于与她取得了联系。我在前边介绍过,她是在“二奶”里头惟一熬出头,升格为港人妇的女子。她告诉我,她已经搬到海湾村附近的一栋新楼居住,正在向湖南省公安厅申请赴港的指标,过港与丈夫团聚的日子指日可待。
“她们好多都回老家去啦,像阿金、阿婷和阿艳啦!要不就到关外打工去了,都不在了,我现在连逛街淘衫都找不到伴啦!”问及当初我们共同认识的“二奶”,佳佳的头摇得像个葵扇,神色黯淡。在她舞动左手强调人去楼空的时候,无名指上的婚戒闪着耀眼的光芒。
在海湾村,“二奶”大为减少,但并没有绝迹,原有的“二奶”还有一些,新“二奶”的面孔又在海湾村浮现。几天来,佳佳向我引荐了三四位新任“二奶”,我在接近、探访、了解她们之后,撰写了一篇《经济不景,港人深圳包二奶也转型》,发往我所服务的报社——香港《文汇报》。几天后,《文汇报》将该文刊发在香港新闻版上,用的是通栏大标题,文章说:
市道不景气带来多米诺骨牌般连锁反应,不仅港人北上深圳购物额度下跌,北上酒楼的次数与消费数额均有大幅度下降,就连夜夜笙歌的酒吧与夜总会,年轻港人的身影也比以往有所减少。更令人称奇的是,港人在一河之隔的深圳包养“二奶”的方式,也随着经济衰退开始了一系列的转型。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继深圳罗湖区某某村之后,深圳福田区某某村,日前居住的“二奶”已大为减少。原先,此地曾经十分活跃,村内每晚莺歌燕舞,百多名各地女子中,有被人包养的新旧“二奶”,还有来自各地的女子云集歌舞厅、发廊,日夜等待前来寻芳的港客。如今,此地已是门前冷落鞍马稀,除了少数几间歌舞厅与发廊还在硬撑之外,有多间发廊已经关闭。一位曾在村内被港人包养过3次的发廊妹透露,现在市道不景气,港人出手不仅没有从前大方,多数还选择和现任的“二奶”分手,有些没有“良心”的港人,干脆溜走不见踪影。
转型之一:月租插水式(粤语:跳水)暴跌
相对于前些年港人包“二奶”一包就包五六年的盛况,如今已风光不再,多数“二奶”的身价大跳水。记者在深圳皇岗口岸附近的两个自然村暗访时了解到,在这两个村子租住房子的“二奶”人数已经大幅减少,租客比往年少了至少两成以上。一位有100多间房产的房东告诉记者,自去年下半年起,房子就不太好租了。今年春节返乡过后,很多“二奶”竟没有回来。听说,有的已经被港人抛弃,但其中仍有人选择死守,结果,拖欠房租高达3个多月。她表示,租到这样的“二奶”就比较倒霉,她只得没收一屋子的破烂东西,不过,就连彩电都是二手货,根本卖不出几个钱。
记者在村中调查时发现,这里门庭较去年上半年孤单冷清。连村内惟一的一家歌舞厅的生意也大不如前。记者曾在此村进行过长达60天的隐性采访,采访过15位“二奶”。如今这15位“二奶”中有半数以上都参加了工作。有的去关外打工,悄然搬走,留下一大堆东西抵充租金。有的应征去桑拿中心当侍应女工或是酒楼的咨客。另外一半已回老家自食其力。
一位叫阿红的女子告诉记者:“现在坐在家中等香港人养的人,都是很幸运的。命不好的就要自己打工。你要是开口要得太多,香港人拔脚就走,不会回头。”记者还了解到,一年前月租价格在三五千元(人民币,下同)的小姐们,全都缩水减半,月租费用均价在一两千元不等。阿春为了补贴家用,选择了自食其力,在酒楼推销啤酒,月入近千元,加上香港人给的1500元,每月收入2500元。她很知足,并没有什么不悦。她认为,经济不好,这已是最好的结局。
转型之二:“终身制”改为“分段制”
一位被港人先后包养过4次的“二奶”小石告诉记者,如今港人包养“二奶”已经没有“良心”了,因为经济不景气,他们不再考虑“二奶”的未来,只顾眼前快乐,大都打破了“终身制”,改为“月租制”或是“半月制”。
港人以前包养“二奶”的程序大多如下:经人介绍后,第一步:与“二奶”在酒楼或是茶楼见面。第二步:租房。第三步:买家具和家用电器。如今,纯粹依靠港人包养的“二奶”已不受青睐,在一些工厂当小文员或在服务性行业打工而且租有房子的女子最受欢迎。港人已全然打破包养“二奶”的基本程序,改为不再租房,只身上门,每月扔下一两千元。据悉,这么一来,不用租房,不用买电器与家具,不用每月提供一定数额的生活费用,节约了一大笔钱。
转型之三:“金屋藏娇”变成“打边炉”
原先一看上某位女子便租房“金屋藏娇”的港人几乎已绝迹,由于经济原因,他们选择了三五好友,合租三室一厅、两室一厅,或者干脆合租一室一厅,这样一来,每月可节省一大笔费用。
阿兰与阿珍是同乡兼同窗。阿兰比阿珍大1岁,也早她一年来深圳。她原先在一家茶楼当部长,后被港人包养。为了能让同窗好友阿珍也能来深圳见见世面,有福同享,她通过自己包养的男人、一位香港货柜车司机出面,将阿珍介绍给了男人的好友、另一个货柜车司机做妾。为替男人省钱,两女人合租一室一厅,每月房租费仅900元人民币,每人只需450元。家具电器除了空调之外,彩电冰箱洗衣机都可以共享。为了多赚些钱,阿珍和阿兰一同去打工,在一家洗脚中心当服务生。阿兰的男人来深圳的时候,阿珍就主动要求加班,将房间腾出来让给阿兰。阿珍的男人来时,阿兰也如法炮制。当然,像阿兰阿珍这样的同乡死党并不少,为港人包养“二奶”“打边炉”提供了种种可能。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有3位同乡合租了三室一厅的房间,纯粹就是为了省钱。3名包养的港人每次同来深圳约会,他们每人每月交房租只需花费400元左右,加上给“二奶”的生活费用,绝不会超过1500元。
转型之四:陪吃陪睡双料保姆浮出水面
一部分回流港人在深圳购置了房产,前些年,他们将自己的房产租给别人,收取租金。为了包养“二奶”,他们喜欢另择它处藏娇。如今,为了节省费用,他们大多收回了自己出租的房产,为了掩人耳目,躲避香港大婆的追踪,改为雇用双料保姆,专为自己提供性服务。据悉,双料保姆不仅要为“主人”煮饭、洗衣服,还要提供按摩、陪吃、陪睡等类服务。一个月来4次,费用约600元人民币。据悉,港人转包双料保姆,绝大多数是图省心省钱。
这篇报道,较早地捕捉到港人在深圳“包二奶”在形式上的变化和变通以及经济不景气对港人滥情行为的影响和制约,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转载、转摘者众,因而被香港《文汇报》评为当年的年度与季度好稿。
因为工作关系,我常到香港去。离开香港,每回从罗湖或者皇岗口岸进入深圳市区,却与众多的港客同时入境。有时候,刚刚过境,看见我身边的香港男士突然加速,与在口岸接客的某一位年轻女子迅速相拥、雀跃,我就坏坏地想,这就是香港男人与在深圳“二奶”的鹊桥相会。有一次入境,望着闸外接客的男女老少,突然间,我好像看见阿金正抱着她的女娃娃,等候她死鬼“老公”的到来。也就在这时候,我想,可以对港人在深圳的非婚生子女展开调查。这批孩子的现在及其未来,对深港两地社会与家庭稳定的影响,绝不能等闲视之。正在我抽不出时间的时候,记者部来了一员生猛大将,实习记者郑海龙先生。我在布置新闻采访任务的时候,把“二奶”子女的选题计划及其要点告诉了他,请他去完成。大约一个星期后,2003年10月5日,香港《文汇报》在A2版整版刊发了郑海龙的两篇文章,一是《港人另类子女滞深边缘化》的长文,副题是《被抛弃二奶所生无钱无户籍求学成问题》,全文如下:
香港近年经济持续不景气,也连累到一些深圳的“黑户”家庭,有原本在深圳包养“二奶”的港客干脆玩起失踪。这使得一些已在学龄的孩子家庭,生活变得日益艰难,这群由港客与“二奶”非婚所生的孩子并不拥有深圳的户籍,需要付出较高的费用,才能让孩子就读当地正规学校。
怕歧视扎堆上学
据了解,经过深圳教育部门审批的港人子弟学校共有3所,另外一所丽中普通小学是以招收港人子弟为主的小学。估计学生总共有2000人左右。有知情者透露,在这些学校就读的“港人子弟”,有相当一部分为港客与“二奶”所生,并无户籍。记者了解到一所仅有300余学生的港人子弟小学,就有248人为港人子女,有297名学生的父母为深圳临时户口,其中港人“黑户”子弟,至少有100余人,占学生总数的1/3。
每学期学费8000元
然而,这些孩子还是较其他同样身世的孩子幸运得多。毕竟不是所有港客“黑户”子女都能够交纳得起每学期8000多元的高额学费。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民政部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整个深圳在学龄但没有上学的港人“黑户”子女,保守估计应在5000人左右,他们的生活十分贫苦,有的甚至识字不到200个,许多孩子最后不得不同母亲回到偏僻的老家,饱受亲友的白眼。
回老家亦饱受白眼
据有关人士透露,自从80年代中期第一名香港货柜车司机在深包养“二奶”以来,如今“二奶”的队伍已经更新为第三或者第四代,甚至更为靠后,在她们进行攀附生活的过程中,也就衍生出大量“黑户”子女。随着“二奶”队伍不断扩大及年轻化,“黑户”子女成为深圳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并日益明显起来。
没有户口,他们就不能继续上学,不能工作,也不能结婚。而即使结了婚,也只能是事实婚姻,没有法律保障。而他们的子女也将继续成为黑户,重复父母走过的路……
另一篇是《港人老爸突蒸发无辜子女受歧视黑户乖女境况堪怜》:
在班主任邵老师的眼中,佳雯绝对是一个懂事的孩子,因此留给人的印象也十分深刻。不巧的是,这个曾经被学校减免一切费用的小女孩,在记者采访前两个月,却因为母亲交不起房租而不得不离开深圳,母女惟有回到湖南老家。
没钱交租惟回老家
邵老师拿着小佳雯入学时候提交的档案介绍,女孩的父亲是一名香港货柜车司机,经常穿梭于港深之间,女孩的母亲则是该货柜车司机的“二奶”。由于近年香港经济持续不景气,她父亲给她们的家用越来越少,几乎不够她们母女在深的生活开支。直到今年年初,男方干脆就不给一分钱而人间蒸发。校方鉴于此种情况,减免了小佳雯一切费用。但在本学期开学不久的一次休假后,邵老师就再也没有见过小佳雯的身影。经联系方知道,她已随母亲回到湖南老家。
房东冷淡见怪不怪
在小佳雯的入学档案上记录着这样一些资料:×佳雯,女,1994年4月生,籍贯湖南,在深暂住东乐花园×栋以及父母姓名和联系方式等字样。记者试图与其原来在深圳暂住地的房东取得联系以多了解一些情况,却被拒绝。而房东的语气似乎也并不很同情这可怜母女的遭遇。
为什么邵老师会特别注意到小佳雯呢?“那是去年开家长会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家长都到了,但是惟独佳雯的家长没有来。正当准备放弃等待时,一个微胖、满面油光、穿着睡衣、趿着拖鞋的女人推门而入,她就是佳雯的妈妈。”邵老师顿了一下继续说,“后来我发现她有些不太正常,三十出头的年龄有些神经质。见人就说自己有多么苦,自己的男人有多么负心。等单独聊的时候,发现佳雯的母亲不是胖而是有些浮肿,且肿得有些发亮。面有菜色,精神萎靡,面对任何人总是重复先前不知重复了多少次的话,有些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
萎靡妈妈面如菜色
“后来我就开始注意小佳雯,其实要说特别,也没有什么特别,因为穿的都是一样的校服,吃的是一样的食堂。惟一不同的就只是别的小朋友是要交学费的,而佳雯则是减免费用。这孩子很听话,也很好学,在学习上从来不要老师费多大的心,非常善解人意,也非常的机灵,一双大眼睛和一对小辫子,消瘦却很惹人怜爱。但是从第二学期起就变了……”邵老师换了一种语气,“我发现小佳雯不太爱说话了,上课也老是走神,下课的时候就默默地趴在桌子上,一句话也不说。没有多久,一次休完礼拜,就再也没有见过她。第二天,我按联系
方式联系,接电话的是她的一个老乡,他告诉我,她们回老家养病去了,从此就再也没有联系。”
老师呼吁救救孩子!
说到这里,邵老师停顿良久:“我是一个打工妹,可能没有权利对这些事情进行批判。但是我要说,因为我觉得只要是有良知的人都应该这样想——孩子是无辜的!在这里我想借助报纸的一角向那些香港的‘父亲’呼吁一声,别忘记在深圳你还有一份父亲的责任与义务!!”
郑海龙在采访的时候,一名30岁左右的湖南妹给了他一封写给香港“丈夫”的信,还留给记者一个手机号码。她希望香港报纸能够发表她的信,希望他能够看到这封信,以期唤醒他死去的职责。这位被抛弃的“二奶”,在深圳已经10年了。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记者发现她正在用“卖春”的钱延续自己的生命,还要养活她和那位香港“丈夫”所生的“阿宝”,并为孩子缴纳那些昂贵的学费。
韩生:
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够看到这封信,在写这封信前我曾经给你打过无数的电话,却总是关机。直到今年的某一天,你的号码作废了,我才真的死了心,我知道我们之间的感情完了。
说来你也许不相信,在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决定和你断绝一切关系了。从此我将独自抚养阿宝成人,因为你在抛弃我和孩子的时候,你就抛弃了你做父亲的职责。这是上天对我的惩罚,谁叫我当初认为跟了你就可以去香港,可以有大房子住,有车开,有一切。
但我错了,其实你什么都没有,有的就是伪装成承诺的谎言。而这个蹩脚的谎言一骗就骗了我将近10年。
也许我们之间根本没有什么感情,也许有的只是相互利用,其实你不是一直这样想的吗?以前的事情我不是很想提了,这是一个只有你我知道的秘密,我想就连你香港的太太也不知道我们的孩子已经上小学了吧。不过值得欣慰的是,阿宝很懂事的,上回考试拿了80多分,老师说他很有进步。
还有就是你不要以为这是我在跟你要钱,我现在可以独自养活我的孩子,我也可以不回老家,不让我的阿宝活在他人的唾沫里。他可以上小学,上贵族小学,也同样可以有快乐的童年。
阿雪
2003年9月5日
香港《文汇报》发表了阿雪的信。
郑海龙在《记者后记》中可怜巴巴地呼吁:“那些曾经在内地留下‘风流种’的港客们,千万不要忘记,你还是一个孩子的父亲……”
简·爱在得知罗切斯特的妻子仍活着时,喊出了《圣经》中的诗人向上帝的祷告辞。她虚弱无助,痛苦迷茫。深圳河畔的“二奶”不是夏洛蒂·勃朗特笔下的简·爱,包养“二奶”的港人也没有罗切斯特的责任心。但在弱势群体“二奶”们漆黑的心里一定也有这样萦绕不去的呼喊,因为,心需要心的爱抚和慰藉。当社会救助机制缺失,那些心无所属、心无可依的“二奶”们,在屈辱、苦痛的沼泽里找不到可以拉她们上岸的绳索,于是,就在冥冥之中乞求神灵的庇护和帮助,喊出简·爱曾经向上帝喊出的话来——
“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急难临近了,没有人帮助我。”
然而,正如尼采说的,上帝死了。
【本文节选自《苦婚》,作者:涂俏著,作家出版社,有删减;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